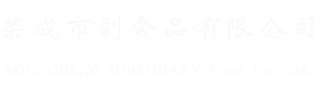我的父亲叫胡光福,号寿康,1936年12月29日出世于湖南省桂东县寒口乡秋里村田垅组鹅井里。
父亲幼时家贫,爷爷奶奶卖柴,大大伯做长工、包月(按月给人家干事)、给做小生意的人当挑夫,父亲到了12岁才去读小学。其时田垅就两个人读书,父亲和陈登亮,两个人结伴上学,校园离家要走一个小时旅程。其时小学是三年制,父亲小学结业后就没再去读高小了,跟着大大伯干事,由于年纪小没有工钱,仅仅有口饭吃。1955年父亲参加了桂东至汝城的公路建筑,挑淤泥清路基。
1956年,父亲应征入伍,后分配到广西桂林,在部队当警务员。父亲在部队养成了吃苦耐劳、大刀阔斧、说一不二、爱规整的武士风格。老家的房子一贯被他收拾得干净利落,各样耕具物品摆放规整,自己的穿戴也从不肮脏,走亲访友还换上新衣服,裤脚会有显着的叠痕。1959年,父亲复员分配到广州铁路局作业,每月薪酬38元。为便利照顾家,父亲1961年请求返乡务农,回家的时分单位发了500元补助金。
我母亲叫罗彩霞,1940年出世,读了高小,其时算是有文化的人。我家兄弟姊妹六人,在上世纪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,全赖爸爸妈妈勤劳的双手,千辛万苦把咱们兄妹拉扯大。
1988年我考取了郴州师专(现与郴州医专、郴州教育学院、郴州师范兼并组建成湘南学院)。当我领到选取通知书时,父亲乐坏了:“儿子考上大学,吃上国家粮了!光宗耀祖了!”快乐之余,父亲也犯了愁,其时上大学农村户口还要办农转非手续,需交纳300斤粮谷、300元钱和3斤茶油。这些我家都没有,父亲曲折借款、拆借,才算在我入学前办好了相关手续。为了子女拼尽全力,这便是父亲。
1991年,我大学结业后留校,家里的境况渐渐好转,尔后就没让爸爸妈妈亲再吃红薯丝拌饭,1995年也还清了大集体时的超支款。天有不测风云,1999年母亲患白血病不治逝世,时年仅59岁。没有了母亲的日子,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家,砍柴种田,清净孤寂。他偶然到咱们兄妹家里小住,可一直不愿意脱离故乡。
2009年10月2日,父亲喜爱在郴州逛街,去公园看热闹,常常恋恋不舍,偶然正午也不回家,就在街边小店吃碗馄饨。
爸爸妈妈年青时分留下些合影、纪念照,母亲逝世后,每逢牵挂她的时分,就只能翻看仅存的几张相片。其时我就想,往后要给父亲多拍些相片。2005年,我具有了第一台相机,从那时起,我就把镜头对准父亲,只需我与他在一同,总会或明或暗地拍下他的身影,把对父亲的感恩融入一张张相片里。刚开始拍时没想太多,便是给往后纪念想。有许多场景我是不忍心按下快门的,比方我嫂子给父亲试寿衣,父亲带咱们去找墓地,等等——咱们不得已承受父亲渐将老去的现实。每念及此,我就会想起父亲捧着手机看母亲生前的视频发愣(这段视频是母亲最终一个生日时,我用录像机拍的,为了便利观看,后转存到手机里),而我又盯着手机里父亲的相片发愣。
2018年2月13日,老屋全景。大伯逝世后,堂哥搬去近邻村,我大哥起了新屋,这么大的老房子就父亲一个人住。
父亲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人,在南边偏远的小山村里,朴素地日子,默默地劳动。但他在儿女的心中又总是巨大的。这巨大源自他对咱们的爱,如家园老宅后的那座山,撑起了家,呵护咱们长大。我常凝睇一张父亲膀子的相片,这双坚韧的膀子,撑起了全家老小的天空。现在他老了,不知道还能为咱们撑多久……
我记载父亲,是想经过印象把父亲所在的社会、日子、家庭情感记载下来,留存咱们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回忆。2020年,《我的父亲》拍照展在东江湖拍照艺术馆展出。开幕式这天,我把父亲请到了现场,没想到那么多人来看,也没有想到我有意无意拍照的相片,在展厅呈现出一种神圣感。观众们给父亲送花,争相合影,老父亲说,这是他一辈子最快乐的一天。
2017年2月4日,父亲用电是从大哥家接线,趁新年二姐夫、妹夫都来了,兄弟姐妹跟父亲一同换电线杆。
每一个日渐老去的父亲,都曾为家流过汗,为国拼过命,他们都应该被铭记,都应该被儿女和社会善待。人们说陪同是最好的安慰,儿女眼中,不该只要对着父亲老去的背影叹气,还应更多四目相望的温情。于我而言,期望用印象点着每个人的乡愁,再续那份暖在心底的家园情缘,更愿全国的爸爸妈妈亲安全喜乐。